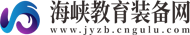【慕洛】山城风
*ooc致歉
 【资料图】
【资料图】
*全文+
*大家七夕快乐!
*被老福特屏了四次,来哔站补档(
米洛一直觉得,他见过风的模样。
那是从山城的小巷深处吹来的风,突如其来地闯入他的生活,紧接着,贯穿他十六岁颠沛流离的夏天。
07年的七月初,米洛从江汉平原那座被称为江城的城市出发,带着一身好闻的樱花味一路西行,在最热的时候往西南群山里的山城去。
他在火车站过完十六岁的生日,没有蛋糕,没有蜡烛,就这么一个人拎着大袋的行李走上火车站台,踩上哐啷作响的绿皮火车的地板,去山城投奔亲戚。车上拥挤,人声鼎沸,参杂着小孩的哭声,令人心烦。
武汉,他生活了十六年的地方,这里有他呼吸了许久的空气和他爱看的樱花。火车开动前他往窗外挥了挥手以示告别——这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往湖北省外去。
对于重庆,他早有耳闻。行千里,致广大,说的就是这座城。他们说人这一生总要看一次嘉陵江的日落,走一次弯弯曲曲不知通向何方的山城步道,总要来这山城走上一遭。曾经米洛无数次幻想过这西南地区唯一直辖市的风光,可如今真的孤身一人踏上开往山城的火车,心里却是止不住的惆怅。
旅途漫长无趣,他闭上眼睛,试图用手捂住耳朵,却依旧无法隔绝小孩哭闹的声音。火车载着一车的吵闹,载着一车不知何处来的人群,载着十六岁的米洛,穿过隧道驶入群山。
绿皮火车大多走得慢,到达时已是下午三四点,一天中太阳最热烈的时候。
拉着行李走出出站口,米洛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一眼看见了一块写着大大的“米洛”字样举得高高的的纸牌,还有一个自己听不出来是谁的声音大喊了一句:“米洛!!请叫米洛的男生到这里来!!!”
有点尴尬。
他硬着头皮往那边走,走到终点发现一个和自己差不多大的男生,嘴里吹着泡泡糖,似乎没想到要找的人已经走到了面前。他轻轻拍了拍男生的肩膀:“你好,我是米洛。”
那人似乎被吓了一跳,吹出来的泡泡“啪”的一声破裂,糊了一脸。
“我是卡慕,你以后的邻居。红叔有事,叫我来接你。”眼前叫卡慕的男生把泡泡糖从脸上扒拉下来,忙不迭补上了自我介绍,最后停住了一秒,似乎在思考什么,“你该不会不相信我吧。”
“信信信,你都知道我名字我怎么不信。”米洛被他说得有点想笑,坐车的疲惫一扫而空。卡慕一手拉住米洛往站外走。卡慕步子迈的大,米洛行李箱的轮子骨碌碌地转个不停。不熟悉的人群与景色都在往后倒退,一时间他的眼睛不知道往何处看,于是仔细打量起眼前的男生来。
被拉着走看不到他的脸,不过就刚刚那两眼就看得出来,卡慕长得怪好看的,难怪人说这川渝地方山水灵,连人都生的标致。米洛的视线现在正对着卡慕的后脑勺。卡慕留了点长发,用橡皮圈箍在脑后轻轻束起一个小啾啾,看着怪可爱,米洛情不自禁地伸手戳了一下,随后又像是想到了什么,触电一般收回了手。
这样子,不太好吧!!!
卡慕突然顿住,相当短暂,以至于米洛都没发感觉,等他自己还没发觉到的时候,眉眼就已经是笑眯眯的了。卡慕没转头,想到身后那个白白净净的男生现在大概率在为自己的小动作没被发现而感到窃喜,心里一阵没由来的愉悦,倒也不能称作什么恶趣味。
他带着米洛等开往十八梯的公交,热浪翻涌,远处的空气都开始扭曲起来。七月初的山城正是最热的时候,米洛望着远处的路面有些出神,再反应过来时被一趟趟人群捂热的公交座椅的温度已经透过薄薄的布料传了过来。
卡慕给他抢下了为数不多的座位,自己抓着车上的铁管站在了米洛旁边,随着颠簸的车厢七上八下。公交车和火车一样,不仅吵,还热空调放出的凉气不一会就被满车厢的人呼出的热气消耗干净,于是有人开窗,山城的风透过窗户吹进来,反倒凉快不少。
米洛看着卡慕站在面前晃来晃去,几次想在逼仄的空间里站起身来把位置让给他,都以失败告终。最后卡慕发现了不安分的米洛,把他牢牢按在座椅上,给他塞过来一个东西。
“无聊的话,听听歌,别老是想着从位置上起来,你是不知道公交车上的位置多难抢。”
米洛听话地把mp3往耳朵里塞,等到音乐声在耳朵里响起来,他又问卡慕:“所以为什么要给我抢位置,我们又还不熟,再说,我可以站着的。”
“嗯......代表我欢迎你,欢迎你来重庆,欢迎你来十八梯。”
耳边的音乐在喧嚣,明明是有些打趣的意味的话参杂着音乐和人群的吵闹,在米洛耳里却格外清晰。
“哈?米洛,你很热吗?脸怎么红了。”
07年七月初,重庆的温度直直往上飙,米洛脸上的温度也直直往上飙。七月的风带着盛夏的山城独有的味道吹进米洛心里。
直到很多年后,米洛还没想明白那是怎么回事。或许人就是容易在孤身一人时对一个关心自己的人产生感情,这种感情暂且不能称之为爱,米洛更愿意把他说成喜欢。他喜欢卡慕,第一眼看到就喜欢,他那么张扬热烈,就那么在那个下午猝不及防地跑进他的心里。
直到很多年后,米洛还是忘不了那天下午,卡慕把带着体温的mp3塞进自己手里,指尖触碰掌心时那种温柔的触感。
他知道,他还是忘不了他的十六岁。
米洛是来投奔自己的舅舅的,十八梯的人都管他叫红叔,又或者是昂口。到这一两个月,米洛也开始跟着这么叫。
十八梯不大,邻里邻居挨得近,谁家有事都互相帮衬着。米洛还挺喜欢这样的氛围。米洛到这没几天就跑到学校办了转学,依旧是卡慕陪着去的。米洛和卡慕不在一个班,卡慕还笑着跟他说哎呀呀好可惜,米洛也开着玩笑嫌他恶心,两个人也熟络起来。红叔工作忙,一个人在重庆打拼也不容易,中午常不回来,就拜托了卡慕一句,又把米洛丢到了卡慕家。
卡慕是单亲家庭。他不设防,大大咧咧地就把父母的事告诉米洛,他说他爸在外头找了个,不要他和他妈了,他妈是外地人,外公外婆又早早去世,房子给了卡慕的舅舅,他们两个没处去,拿着身上仅有的钱买了十八梯最便宜的吊脚楼,就这么草草住下。
米洛觉得他可怜,话在肚里弯弯绕绕最后还是没说出来,不合适,他也不会去干这种事,倒是卡慕反过来安慰他,说自己早就习惯了,有没有爸都一样,他过的很好。末了还要加上一句:“尤其是交到了咩洛sama你这个朋友,就更好了。”
米洛这两个字和卡慕的重庆口音撞在一块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化学反应,不知什么时候米洛的名字就变成了咩洛,sama从不知道是卡慕看的哪部动漫里头蹦出来,变成了咩洛的后缀。
于是米洛也回给卡慕一个敬称:“去你的吧卡慕sama。”
他还和米洛说了一堆好玩的事,比如说王大爷有一次坐在巷子口扣脚趾头,比如说以前自己偷偷把零嘴藏在门口的花盆背后一个星期没被发现,再比如说红叔经常被隔壁家李婶催婚,什么事都有,他也会用一种鄙夷的语气和米洛说这条鱼小巷上也有些不可理喻的人,让米洛少惹他们。
他还会问:
“米洛啊,你知道十八街的名字怎么来的吗?”
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后来我上网去查,网上说原先十八街有一口井,附近的居民去打水要爬十八级石梯,所以叫这里十八梯。还有一种说法是这里的台阶断断续续十八段,具体那种对我也不知道,总之都说是老一辈口口相传下来的。”
那重庆是个什么地方呢?
“重庆嘞,分上半城和下半城;十八街嘞,就是这上半城和下半城交界的地方。”他会随手在地上捡根小木棍,用它画一画,奈何小木棍不给面子。“啪叽”一声断掉,于是他就会把木棍丢在一旁用手比划起来。
“重庆山多,你们外地人不是给重庆取了个山城的名吗?这地方,走路能比骑自行车方便,冬天湿冷冷到骨子里,夏天给你热成蒸笼,有条嘉陵江流到天边,汇到长江里去。
哦对了,你们还给重庆拆成了一句话来着,行千里,致广大对吧?别的我不知道,不熟悉路的话一天在重庆可能真的能行千里。”
一番话颇有些带着同学入坑某游戏时恐吓新手的味道。
卡慕还和米洛说,自己很久没和别人说过这么多话了,俨然是已经把米洛当成了最好的朋友。
两个人打打闹闹,这个暑假过得倒也快乐,快乐到米洛根本不会去想自己的父母和家庭那些臭事。当然,最后几天卡慕拉着米洛疯狂补他欠下的暑假作业的时间除外。
人们喜欢用秋高气爽来形容九月之后的时光,然而九月的重庆并不凉快。
教室里的风扇都摇摇欲坠,更遑论空调。米洛一直没好气地吐槽,说学校光顾着高三,不给高二生也安排一个好点的环境。汗珠从额头滚落下来,哪怕是拼了命去扇风也没有任何用处,大概等熬到十月才能好起来。
卡慕喜欢去找米洛,米洛也莫名地期待起每天下课各种各样的“偶遇”来。换了陌生的环境,任谁都会想和熟悉的人在一起。米洛想起来一个很有意思的词语,叫雏鸟效应,说雏鸟会把睁开眼睛看见的第一个人当成自己的妈妈,就像人在一些时候第一个遇到谁,就会对谁抱有一种莫名的好感。这么一想,他还觉得这效应挺有道理的。
至于卡慕天天往米洛那跑,还有一个原因是,米洛总说自己在班上没交到一个朋友,他们都不怎么理会自己。
米洛喜欢卡慕这样开朗的人,原因很简单,跟这种人待在一起,感觉整个人都会开心起来。
偶尔用着恶心人的腔调说着恶心人的话的时候除外。
开学没多久学校就筹办运动会,时间定在十月底。放学路上卡慕异常兴奋地告诉米洛班上的同学把一千米长跑推来推去,最后推给了自己......是的,异常兴奋。
米洛问他,你脑子是不是有什么问题。
他说:“不是,想到你会来给我加油就很兴奋,想一想,你在人群里大喊我的名字,就像那天在火车站一样。”
所以米洛又回:“去你的吧,我才不会干这么傻的事。”
结果在比赛那天,却是老老实实带着啦啦棒站到了跑道旁边。
07年的十月底的下午,阳光明媚,天空晴朗,真正称得上是秋高气爽。米洛穿着卫衣站在人群里,听着一声急切的哨响,然后看着一排的人冲了出去。
队伍里那个辫子一跳一跳的身影格外显眼——卡慕又把头发留长了不少,为此没少挨老师的骂,却依旧是我行我素,米洛觉得他挺勇敢的。
每次跑过米洛的位置,卡慕都会分心去瞟一眼,去听米洛那分贝不大还混杂着自己班上的同学的呐喊声里的“加油卡慕”。嗨,明明只是开个玩笑,他还真的当真了,卡慕觉得米洛格外可爱——他自认为这是一个相当中肯的评价。
米洛确实很可爱,他有的时候会这么想。
被他打趣到脸红时可爱,口是心非的时候可爱,坐在那里发呆的时候可爱......卡慕不觉得这对男生是贬义词,正相反,他很是喜欢用这个词语去形容米洛。
哦对了,米洛听到这个词语的反应也可爱。
他会一边说“可爱你妈啊卡慕,老子可爱给你看”,一边抓起书或者什么东西往自己这边扔,然而扔到身上的力度却轻飘飘的,再仔细去看就会发现米洛的嘴角其实是笑着的。
卡慕不是第一名,但也没关系,班上的同学依旧会围上来问他感觉怎么样,给予他站上跑道应有的夸奖。卡慕坐在座椅上猛地喝了一大口水,突然发现米洛并不在人群里。
这是今天下午最后一场比赛,学校也不补课,米洛或许是先回家了。
他又问了一句,你们看到隔壁班的米洛吗?
没有啊,好像被他们班的李林几个人叫走了吧?
卡慕突然站起来跑出去,来不及顾及腿上的酸痛。
“诶等等,再坐一下啊??你水还没拿!!”
他不会忘了这个名字的。
他在学校没几个要好的朋友,最初的原因还得追溯到这个李林。他也住在十八梯,听母亲说是花钱买的高中上,从小就不学好,家里本来就没几个钱,全都被他浪费掉。卡慕以前长得小,跟着母亲过了段苦日子,刚搬到十八街就被盯上。少年时代的记忆清晰又残忍,他记得那天他不要命地捡起地上的瓦片往那人头上丢,他没注意有几片丢中了,他只知道他们两个最后都挂着彩回了家。
那个怂货没敢再来找他麻烦,只是每每遇到他都会白上一眼,许是从小到大第一次被人这么揍。
直到后来,高一军训他和李林在一个班,搭话任何人都不理他,好不容易抓住一个初中同学,才知道李林去跟别人说谁和他玩他揍死谁。
相当幼稚的报复方式,以至于卡慕一度怀疑他是不是脑子没发育完全。因为这件事李林也没交到朋友,顶多多了几个见风使舵的小弟,最后也就不了了之。
但米洛不一样。
他知道米洛有一堆心里话没说,他感觉得到米洛没那么坚强,他也知道李林看见过米洛和他一块回家,所以他一点都不放心米洛待在那个班,于是专门往米洛那跑,生怕米洛被欺负。
他直直跑出校门,在巷子里穿行。学校附近是拆迁区,一个个鲜红的拆字刷在墙上,在他的视线中向后退去。身后带起一阵阵风,把他的头发都吹起来。
红叔交代过他要照顾好米洛,妈妈也说米洛看着内向别让他受欺负,所以他不敢停下,不敢......
米洛被他们堵到墙角的时候一直期待着有一个人可以来救他,救他走。
拳头如雨点般落到身上,好痛。
他不知道他们为何对自己的恶意那么大。他听说过卡慕与李林的事,于是他在班上几乎绕着李林走,但人与人之间的恶意总是来得突然,霎那间就贯穿心脏。
“你不是和他关系很好吗米洛?”
言外之意就是,
那他欠我的,你来还吧。
他的意识开始模糊起来,朦胧间他好像看到了爸妈,他们也在吵架,在动手。现在的他就像那个时候靠着房间门默默聆听、默默流泪的他,那么软弱,那么无助。
好像有自行车驶过来了,车链条被人骑得咔咔响,好像下一秒就要断裂抛锚。
是谁啊?
是来救我的吗?
等到米洛意识回笼,那群小混混已经不见了。现在他被卡慕搀扶着,一步一步往外走。
卡慕脸上挂了彩,一道血口子从耳根划到脸颊,米洛不敢去想他经历了什么。
“我先带你回去休息,明天我就去告诉你们班的老师。”
“不要,”米洛强撑着稳住身子,“我想去看嘉陵江。”
米洛一直想看嘉陵江,他想知道这条江和江城的江比起来有什么不同,更长吗?更美吗?他不知道,所以一直想来看看。
十八梯离嘉陵江边不远,但夏天天热,等凉快下来学业又重,他曾经远远的望过,却从来没有真的走下那层层叠叠的台阶,走到伸手就能触碰到那片水域的地方仔仔细细的看一遍,说来真是不应该。
“你应该去休息。”卡慕的语气难得这么决绝,米洛却不以为意:“卡慕sama,我没那么脆弱。”
卡慕也难得拗不过米洛,他把自行车扶好,让米洛坐在后座上,往江边驰骋而去。
07年的风把米洛吹到山城,把卡慕吹到他面前,抚平了他被家庭一刀一刀剜得血淋淋的伤口。
他发现自己爱上山城了,爱上山城的风,山城的江,爱上天上飘过一片又一片的云,鸟飞过高高低低的楼房沿着嘉陵江往远方飞,爱上山城的少年,义无反顾地沉陷其中。
难怪他们说一定要去看一次嘉陵江的日落,只有亲眼看过才知道,山城和落日多么相配。像是上天把橘红色的颜料撒在水里,让它随着水波的流动四散开来,染红天边,染红天边的云,染红流到天边的嘉陵江。
米洛感觉身上的每一处都在隐隐作痛,但显然是看到美景的震撼胜过了疼痛,此刻的他完全感受不到,他只知道,
这真美。
山城真美,重庆真美。
他转过头去看卡慕,卡慕没发现注视着自己的目光,他只是托着脑袋,盯着水中残阳的倒影。
“卡慕,我觉得,认识你真是件很幸运的事情。”
“我爸做生意欠了一大笔债。在我十六岁生日的前一个星期,我爸跳楼了。
我妈不要我,她说还有人追着她要债,她要逃去别的地方,不能带着我。但我很清楚,我妈从来就不喜欢我,她和我爸结婚是被迫的,生下我也是被迫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不在武汉,身体也不好,他们就商量着把我送到远房亲戚家,就是红叔这。
你知道吗卡慕,四个月前,我自己在车站对自己说了一句生日快乐,那个时候我觉得,世界上应该再也不会有人爱我了。”
卡慕有些沉默,这不多见。
“不是这样的。”好半晌他才幽幽开口,
“你有我爱你。”
“哈?这算什么?表白吗?如果是的话,我也喜欢你哝。”
随便你喽咩洛sama。
卡慕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回的。
少年的爱很简单,简单到只需要一个眼神就能到地老天荒,一句承诺就能当海誓山盟。
那天人不少,卡慕却在江边义无反顾地抱住了米洛。两颗心脏隔着两层薄薄的血肉贴在一起,卡慕能感觉到米洛胸腔里有力的跳动,以及把头埋在自己肩膀时低低的啜泣。
卡慕说,
米洛,明年我给你说生日快乐。
米洛其实并不愿意承认他和卡慕是那种关系,他怕身边人发现,一直避着卡慕他妈和红叔,但卡慕愿意。
他来找米洛的次数更加频繁了,有时甚至嚣张跋扈地走进米洛的班级,大摇大摆地从李林面前过,衣角擦过桌面的时候还要白上一眼——卡慕把所有事都告诉了红叔和母亲,两个大人特地请假跑到李林家,把他父母和他全部劈头盖脸骂了一通。
他父母还是蛮好讲话的。
而且李林头上缠着纱布在一旁低声下气的模样真的很好笑。
那之后他们没被找过麻烦,米洛也不再想理他。李林在没用带着恶意的眼神打量过米洛,兴许是怕再被揍一遍——米洛听说他在家还被父母揍了一通。
红叔的工作依旧忙碌,他最近谈恋爱了,对象是四川人,也是在重庆打拼的,米洛那这件事打趣他,红叔都懒得理,反而是寒假放假时他问米洛:“米洛,半年多了,你应该没什么不适应的吧?你要过得不好我可没法交代。”
米洛在写作业,听到这话停下笔:“那倒没有。”、
话锋一转,他又问:“昂口,我看你之前带回家那个姐姐挺好的,什么时候有结果啊?”
“去你的吧小兔崽子,叫我叔叫小雪姐是吧,滚滚滚......再过一段时间,至少要等我攒够买戒指的钱再求婚,到时候请你和卡慕吃小蛋糕。”
“好啊昂口,我等你。”
那倒没有后面一句话他没说。
他想说,不仅没有,我还很喜欢这个地方,很喜欢这里的人。
其实本来就喜欢的,他是平原长大的孩子,看到连绵起伏的群山,当然喜欢。虽然来重庆半年,他还是没有搞清楚四通八达的小路,没搞清楚哪家的小面好吃,没搞清楚悬在天上的轻轨哪条线到哪里去,也没搞清楚那些复杂的城区。但他还是喜欢这里,喜欢山间吹来的风,喜欢纵横交错的小道,喜欢那句“行千里,致广大”。
他最近很少再想起父母的事了,因为生活里有个显眼的人更值得被他倾注更多注意力。
跨年夜的时候卡慕把他拉到自家吊脚楼的顶层,只有他们两个,搬着条小凳子就坐在露台,冷风刮在脸上生疼。但卡慕却借着微弱的天光,捧着时钟掐着秒,等到零点整,他对米洛说,
“米洛你看。”
烟花从远处的江边升起,不用想也知道嘉陵江现在被染成了何等绚丽的颜色。米洛笑他就为了这个吹了这么久的冷风,卡慕就告诉他一年难得看几次烟花,和他一起在跨年时看更是第一次,意义不一样。
米洛嫌他恶心,卡慕就说,既然都这么恶心了,那就再恶心一点,把脸往米洛那边蹭,嚷嚷着到现在米洛还没请过他,这么特别的日子,要米洛亲他一口。米洛一把把他的脸推开,他就不知从哪里掏出来一个相机,米洛看着他一边调快门一边喊自己看镜头,说在不快点烟花就要放完了。
他知道卡慕喜欢拍照片的,他被卡慕拉着参加了不少摄影社的活动,以此为由卡慕拉着他照了不少照片。他用的是从二手市场上淘来的数码相机,老型号了,但依旧乐此不疲。米洛不乐意上镜,还是被拉着拍了许多张。
“来,茄子。”
“茄子。”
这次米洛没有躲开,他想着,就这一次,随便他怎么拍。
“现在是2008年1月1日,以后,也要一直在一起。”
米洛笑了,自己都没发觉到。卡慕按下快门,正好抓拍下烟花绽放的最灿烂的瞬间。
高中生的日子漫长,枯燥,却也时时刻刻令人欢喜。老师习惯于给高二的学生灌输高考即将来临的紧张感,坐在教室里的人却依旧保持着在课堂正襟危坐,下课后就抛在脑后的状态。
当然,学还是在认真学的。
米洛对卡慕说过不止一次,以后想去上海的大学,去看外滩的繁华,去看那座一步一步崛起在中国东部的大都市,然后他们定居在上海,去养一只猫,或者一条狗,过自己的日子。
米洛还告诉卡慕,他很喜欢一些带着文学性的东西,比如说,他一直觉得信是一种很神奇的通话形式,可惜现在的人更习惯用手机发短信。卡慕就笑着说以后自己写封情书给米洛,是不是能把米洛感动的不要不要的。
日子似乎在一天一天好起来,至少对米洛来说是这样的。他会在放学云霞满天的时候拉着卡慕走过长街,一遍一遍地去描摹所有有可能的未来。放在一年前,这是完全不可能的事情。
四月份,天气开始回暖,巷子里砖墙脚的野草又发了疯一般生长起来。这个时候卡慕开始问米洛,他说,米洛啊,你喜欢什么礼物,我给你准备。米洛敲他脑壳:“还有三个月嘞。再说哪有人送礼物还问的。”
卡慕也就摸摸被敲的地方——其实并不重,他就是喜欢做做样子:“不告诉就不告诉呗,敲什么。”
米洛也以为这样的日子会持续下去,至少在五月初之前他是这么想的。暴风雨来临之前永远是晴天,谁也不知道下一秒乌云会密布天空,遮住耀眼的太阳光。
“你赶紧回去,要不昂口该担心了。”卡慕站在家门口,朝米洛挥挥手,然后推开门走进去。
本来心情很好,直到他看见母亲看自己的眼神不对劲。
他还在打着哈哈:“我亲爱的妈妈,怎么了?什么事惹你不高兴了?”
直到他妈示意他坐在凳子上他才觉得不对劲。
“你和米洛什么情况?”
我幸幸苦苦养你到这么大是为了让你当同性恋?你们爷俩是不是要弄死我?”
卡慕的脑子有些发懵。
“你不是答应过妈妈不当同性恋吗?你怎么了,啊?你怎么了?我和你爸离婚的时候你不是也说他们恶心吗?卡慕你告诉我,米洛给你灌什么迷魂汤了?啊?”
卡慕从没见过自己的母亲这么失态。他和母亲一直都告诉别人离婚是因为父亲在外头找了个女人,他从来都知道不是这样的。而且,从小学父母离婚起,他记忆里的母亲就是温和的模样,对自己是这样的,对邻居是这样的,对米洛也是这样的。
“我不是,我没有......哪来的?”他那张向来伶俐的嘴此刻突然失了语,因为他的母亲把两张照片拍到了桌面上。
上面的人像很模糊,却也看得出是谁,两个人脸贴着脸,不用细想也看得出是在干什么。
卡慕记得,某天他和米洛在小巷子里走着,他跟米洛开玩笑,要米洛亲他一下。他以为米洛不会动的,只当开个玩笑,结果嘴唇上突然就贴上了两片凉凉的东西。
他脑袋有些晕乎,这条巷子走的人本来就少,卡慕根本没注意后面有没有人。
“现在开始,好好学习,不要再和米洛有任何来往,我给你办转学,等这个学期结束我们就搬家,房子我已经找好了,不贵。”母亲深吸一口气,语气平静得可怕。
嘛的,沙币一个。
卡慕不管不顾身后的骂声,跑出门去,他要去找李林。卡慕以为那件事之后他就不敢造次了,谁知道背地里心眼子多得很,知道他们两关系好到不正常,就天天带着个破旧的拍立得,就等着那天抓他们的把柄。
他看到米洛就在门外,米洛走的不快,刚走出不远就听见卡慕家歇斯底里的喊声,缩在吊脚楼与吊脚楼小小的间隙里发抖,两个人四目相对的瞬间,米洛立刻站起身跑回家。卡慕没看到从米洛眼角滑下的眼泪,也没有去追,他不知道怎么和米洛说。李林就在卡慕家附近瞎晃荡,他只顾着揪住李林的领子,然后输出一连串他平时想也不会想的粗鄙至极的方言。
他还去找米洛,红叔在家,却把卡慕拦住了,他说米洛一回来就说想睡觉,让卡慕别去打扰他。卡慕转过身要回去的时候他听见红叔叹了口气。
米洛没睡着,他听见卡慕在外头,但他不想出去。
那天之后他们的关系突然像被斩了一刀,毫无线索地直接断开。
他不敢再去找卡慕了。米洛开始提前半小时往学校走,以求避开卡慕,还是被卡慕缠上,卡慕还是粘着他,用那种恶心的强调和他说话。但这次,米洛是真的觉得恶心了。他说,
卡慕,你觉得我恶心,那你那个时候回答我干什么。
不是的,不是这样的,不应该是这样的。
米洛没再理过他。
好冷,明明是五月份了,却像一月份一样,寒意钻过衣服直往骨子里去。
他好怕,他想起来在他很小的时候父母吵架,妈妈赌气离家出走,过了一天一夜才回来,回来那天爸爸又骂了他一顿,说是他不听话才把妈妈气走的,他那天一直哭,妈妈回来了就扒在妈妈身上哭,鼻涕眼泪糊了妈妈一身,却没得到一句安慰。
那天起他开始习惯蜷缩在床上,把自己盘成一团,小小的空间能给他莫大的安全感。来十八梯之后米洛的睡姿愈发狂放起来,现在的夜晚,他却又把自己蜷缩在了一起。
没有卡慕的两个月,似乎难熬了很多。
下课后米洛会习惯性的看向门外,再没有那个熟悉的身影。关于高考的鸡汤一碗一碗被老师灌进肚里,夏天的风也一点一点燥热起来。米洛没再主动找过卡慕,卡慕他妈说的话他贴在门外都听到了,他想不明白,也不愿意想明白。
为什么他说着同性恋恶心还要来骚扰自己呢?为什么明明前一天还对自己那么好的阿姨后一天就冷眼相待呢?为什么呢?
他终于明白为什么有人说山城是一座遗憾很多的城市。山城的路太绕,以至于还没看见曙光人就走散在弯曲的小道,还没成熟的感情朦胧中就被风吹散,不知何去。
六月底学期结束的时候卡慕他妈就带着卡慕搬走了,像老鼠遇见猫一样避之不及。米洛没出去,就趴在自己房间的窗户前看着外面搬家公司把大包小包的东西往十八梯外搬。他没看见卡慕,事实上这两个月他们都没怎么见面,哪怕在路上碰到也只是淡淡的互相看一眼,然后擦肩而过。
好遗憾啊,米洛突然想到,心底涌上一阵莫名的悲凉,他还没听过卡慕对他说生日快乐。
等搬家公司离开已经接近中午,米洛推开门出去,看见红叔一脸高兴地坐在外头,餐桌上摆着两个小蛋糕。
“求婚成功了?恭喜啊昂口,百年好合。”
“米洛不错,有眼力见。”红叔开心得像个孩子,“答应你的小蛋糕,赶紧吃,待会奶油要化了。”
“可惜了,回来晚了一步,卡慕是吃不到了。”
米洛拆开包装用叉子送了一小块进嘴里,好甜,甜的发腻。
一年过得很快,米洛也早就适应了没有卡慕的日子。卡慕现在在哪,他不知道,大概在这座城市的另一头过着与之前完全不同的生活,米洛不愿在意。无法否认,卡慕给他的影响是大的,至少他现在可以平静地面对自己那断壁残垣的家,面对自己颠沛流离的十六岁。只是有的时候经过无人的小巷,有时压力大去江边散散步,他的眼前都会莫名浮现出那个扎着小辫子的背影。
他伸手去戳那个小啾啾,就像第一次见到那个人时他干的那样,可下一秒人影却无影无踪。
米洛的高考成绩出乎自己的意料,想去的大学肯定是能报上,可填志愿的时候他突然停住了笔。
“到时候,我们一起去上海,过我们自己的日子。”
他最后选了上海的学校,不为什么,实现一个不可能再完成的约定也好,满足自己的愿望也罢,无所谓了。
十八梯要拆迁了,红叔在新城区贷款了个房子,打算再过一段时间就和小雪结婚。米洛临走的前一天,一封给米洛的信送到了十八梯,在这个已经开始流行短信的年代,一封信,实在少见。
米洛知道那是谁送来的,只是忙着整理行李没有拆开,第二天他去赶火车,去的还是来时的那个火车站,坐的还是来时的那款绿皮火车,还是和来时一样,一个人踏上了旅途。
米洛拆开了信封,他知道那是卡慕的字。明明说好不再理他的,大脑却控制着手翻开纸张,控制着眼睛观看起来。
“如果你们还没从十八梯搬走,我还没记错十八梯的地址,你应该能收到这封信吧。”
“米洛,对不起。”
“......我一直没和你说实话,我怕你疏远我。挺可笑的,现在我们却形同陌路。”
“我没什么好说的。我考得不错,你一定也是。大学四年我选了北方的学校,你应该不会去北方吧?”
“以后还会再见吗?我不知道,你大概也不想见我,我也就不去烦你了。”
“......信封里有张照片,给你,记念我们荒诞盛大的十六岁。”
“对了,你收到信的时候生日应该已经过了,送你一句迟来的生日快乐。”
“好好生活,以后多保重。”
卡慕扯西扯东写了满满一张信纸,让米洛恍惚想起来高二放学时他们也是这样,扯西扯东就走完了从学校到十八梯的路。
他从信封里抽出了那张照片,他记得很清楚,是那年跨年的时候拍下来的。照片上的他笑得灿烂,身后的烟花也开得绚烂。他突然很想打开车厢的窗户,最后一次,趁着火车还没驶出这座山城,再呼吸最后一次重庆的空气。
他之后不会再打算回来了。他的家最开始在湖北武汉,后来变成了西南群山里的重庆,现在,他要漂泊到上海去,从此以后,估计就在那儿落叶生根了。
群山再往后退,再驶出最后一个隧道,他就不再身处这片山了。他突然发现自己还是舍不得这里的一切,舍不得夏天吹过燥热的风,嘉陵江里夕阳染红的倒影,舍不得十八梯的青砖绿瓦,舍不得他。
要怎么学会忘记。
要怎么忘记一个人,一件事,一座城。
要怎么说服自己,要怎么把一切都放在回忆的角落里,等他变得不痛不痒,最后再一点点去忘却。
要怎么放下想念。
要怎么学会长大。
在这之后他会用很多很多个夏天的时间去思考问题的答案,或许彳亍于原地,或许开始往前迈步。
他不知道自己以后还会不会见到卡慕,不知道未来他会遇见什么,不知道自己应该做好怎样的准备。
车厢依旧吵闹,驶入隧道时,窗外被黑暗笼罩,车窗上映出米洛自己的脸,他伸出手去触摸,指尖上传来冰凉的触感。照片平摊在桌上,他想起来,那天晚上卡慕趁着自己不注意,凑上来吻了自己的额头,还郑重其事地说:
“米洛,我爱你。”
2016年,十八梯正式开始规划重建布局。
米洛在上海上了四年大学,2013年毕业后他打了几份工,后来做起了游戏博主,算是小有成就。红叔在重庆过得不错,和雪姐的小日子也美满幸福,他这几年很少回去,除了新年回去算个阖家团圆。他也再没见过卡慕。
2016年七月初,米洛从新闻平台刷到十八梯要拆迁的消息,他刷手机的手愣住了几秒钟,随后一个冲动就在网络上订购了去重庆的机票。飞机落地,米洛随手在路边打了辆的士,直奔十八梯。
山城早已今非昔比。新城区的面积扩大了几倍,绕来绕去的路线更加复杂,现在的他更分不清哪条轻轨会通往那个地方了。十八梯早已没什么人居住,六年前决定要不要拆迁的投票结果一出,大家就陆陆续续往外搬了,现在还留着的大多是老年人,打算守着陪了自己一辈子的屋子到最后一刻再搬走。
有个大爷认出了米洛,米洛记得他,原先和卡慕对门的大爷,常招呼他们俩去家里吃小零食。
他说:“哟米洛,好久不见嘞,小娃娃终于记得回来看一看了啊。”
他说:“嗯,我回来看看。”
07年到现在有多久了?
九年了。
大概只有山城的风和奔腾的嘉陵江水还没变过,其他的人,亦或是事,全都变成了他不熟悉的模样。
他还去了一趟嘉陵江。
依旧是夕阳西下,江水被染成红色,这次一同被染色的还有周围高楼的玻璃幕墙,景色愈加瑰丽,江边的人也比九年前多上不少。
江边的栏杆换了新,他撑在上面,似是在发呆。
他的脑海里突然又浮现出那个身影,他发现他还是忘不了卡慕。
山城的一草一木,一呼一吸,都让他心里的那个背影又明晰几分,他深深叹了一口气。
“卡慕,今天是我的生日,祝我生日快乐。”
“你最近怎么样,还好吗?从2009年到2016年,我们有七年没见了。”
“我过得很好,不用担心。”
“还有,我好像一直很爱你。”
他自言自语般说了很多,从晚霞站到星星爬上夜空。
江边人来人往,没有人会在意他在干什么。
眼泪好像又不自觉地从眼眶里滑了下来,他抬起手去擦,越擦越多,最后糊满整个视线。
起风了,风从他身侧吹过。
朦胧间他似乎看见两个少年,高一点的后脑勺扎着小辫子,矮一点的是他自己。
那是他颠沛流离的十六岁,
是他永远在等候的、一场来自山城的风。
标签: